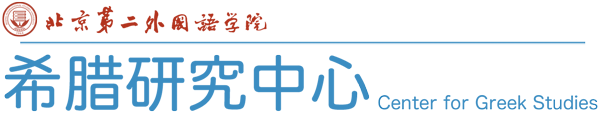讲座纪要:
在讲座开始,黄薇薇老师向大家介绍了参与此次讲座的王双洪老师、吴明波老师和李向利老师,对各位老师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王双洪老师来自北京社科院哲学所,主要研究古典政治哲学和古典诗学,先后致力于柏拉图、古罗马诗学等研究,近两年开始关注培根。吴明波老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攻古罗马研究。李向利老师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古典政治哲学研究。黄薇薇老师指出,就内容而言,“大西岛”一名曾在柏拉图(Plato)的《克里底亚篇》(Critias)中出现,与古典传统颇有渊源;就形式而言,《新大西岛》(New Atlantis)是一篇未竟稿,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思考之域。《新大西岛》大体讲述了船员在海上漂泊,无意间在上帝的指引下来到了一个虚幻的岛屿的故事,该题材使读者联想到荷马、斯威夫特、莫尔等人的作品,亦引起读者对中国古典作品中桃花源一地的浮想。
王双洪老师首先介绍了培根的生平经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626年),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曾任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要职。培根生活的年代处于英国的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王权、宗教势力和资产阶级新贵三股势力处于此消彼长的斗争和变动。在这一背景下,培根为政治共同体寻找新的平衡状态。施特劳斯( Strauss)将培根和霍布斯(Hobbes)称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思想的继承人和推进者。提及现代生活和政治原则,我们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霍布斯和洛克(Locke)身上。但是,培根作为现代事业的推动者,亦不可小觑。
王双洪老师表示,之所以将《新大西岛》称为“现代乌托邦的科学寓言”,在于培根在用故事描绘一个由科学建立起来的理想城邦。培根关于科学与政治、科学与宗教的观点非常大胆,在王权和宗教权力强大的时代,他把科学的重要性和权威放在了王权和宗教之上。故事讲述船员在本撒冷岛的见闻,王双洪老师将《新大西岛》分为“遇难船员听到的讲述”、“提桑家宴”和“萨罗门学院元老的接见”三个部分。上岸之后,船员们发现岛上的人也信仰基督教,由此获得了安全感。本撒冷岛立法者做了两件重要之事:其一,确立了外人不可以进入本撒冷岛,该条法律是为了保护本撒冷不被外人所知;其二,建立萨罗门学院。萨罗门学院是科学研究机构,研究万物本质,又名“六日工程学院”,与“上帝六天之内创造天地万物”相呼应,有建立天国的意味。之后,船员受邀参加提桑家宴,这是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习俗,赞美丰产与富足。萨罗门学院的院士在十几年之后再次来到这座城市,受到民众井然有序的迎接。王双洪老师指出,培根对当时场景的描述,就像描述门徒们在迎接宗教首领。院士接见船员,向船员们介绍了萨罗门学院创建的目的、院士们的分工等。萨罗门学院意在“拓展人类生活的边界”,他们可以干预动植物,甚至可以控制风、雨、雷、地震等自然现象。。
王双洪老师指出,培根将作品命名为“新大西岛”,与柏拉图笔下旧世界的大西岛相呼应,众多研究培根的学者将《新大西岛》视为柏拉图作品的模仿、修正。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中,根据对话者转述的传说,雅典曾经拥有最好的城邦制度,雅典曾领导全希腊人取得了胜利,但后来雅典人经历了多次的地震和洪水,就沉入了地下,亚特兰蒂斯也沉入了海底,《蒂迈欧篇》中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讲述就到此。在《克里底亚》中,雅典人和亚特兰蒂斯人都是神的后代。神为亚特兰蒂斯人划定了区域,但他们修建庙宇、王宫、港口时努力超越前辈的范围。波塞冬为他们传下了礼法,属神的本性让亚特兰斯人温和睿智,不会因为财富而迷醉放纵。但是,当属神的本性逐渐消散,属人的本性便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之后,亚特兰蒂斯人就开始变得贪婪。于是,宙斯召集众神意欲惩罚他们。到此,柏拉图的《克里底亚篇》亦以尚未讲完的形式结束。王双洪老师认为,柏拉图的对话表明只有属神者才能拥有完美的城邦,人是无法生活于完美城邦中的,城邦会因人的不完美而遭到神的惩罚。总之,在形式上,培根的《新大西岛》与柏拉图的《克里底亚篇》都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寓言;在结构上,两部作品都是未竟之作。虽然新、旧老大西岛都是完美的,但结局不同: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大西岛的结局是毁灭,而在培根笔下,大西岛似乎是永恒的。新大西岛在科学上不断进步,但政治和宗教方面似乎是静止而恒在的。
在《新大西岛》中,本撒冷学院是一个能改造自然的科学机构,学院的院士们已经掌握了规律,能使得新大西岛人避免自然灾害。同时,他们有各种应对战争的武器,有可以帮人减少病痛、延年益寿的发达医学。在王双洪老师看来,本撒冷学院的院士们拥有科学这一至高权力,从而统治着整个共同体。本撒冷公民的秩序源于对科学的依赖,甚至是恐惧。王双洪老师阐明,培根在文中尚未提到城邦的德性。《新大西岛》中,基督教的信仰为科学所用,是科学创造了本撒冷的乐土。王双洪老师认为,在文中,家宴这一庆典的秩序来源于父权,因为提桑拥有极高的威望和权力,是维护秩序的关键。本撒冷有两种崇拜,其一是自然习俗中的提桑,其二是政府自然的萨罗门学院。无论是政治,宗教,还是自然习俗,都从属于科学统治的需要。
基于以上解析,王双洪老师总结道,古典的乌托邦主义否认理想政治会在现实中存在,而现代乌托邦则试图实现这样一种理想。柏拉图在作品中提醒我们,如果政治生活消弥了理论和现实的张力,那么人类的处境就会面临混乱和危险。培根站在现代科学的开端,要建立一种人类在自然面前绝对自由的科学共同体。然而,科学无法为人类提供道德标准。《新大西岛》中的科学超越政治,又需要政治。培根身处现代事业中,隐约意识到了现代科学在解放人的同时,也束缚了人,我们应对科学保有足够的敬畏。
黄薇薇老师:
双洪老师对培根的引鉴,切中重点。在研究培根时,我们一般会关注他在现代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能并不清楚他在整个人类思想史,或者说是现代启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双洪老师以现代科学的发展之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引入培根的《新大西岛》,向我们阐明了培根的思想史意义。
培根要求人认识自然,寻找自然背后的规律,并以此进一步改造自然。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权力)”,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去改造自然,改造生活,而“改造”的根本目的则在于让生活变得更为容易和便利。如双洪老师在讲座中提到,在新大西岛上,科学或一切行动的目标无非是延年益寿,使生命长存,而这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存在极大的相似之处。就这一点而言,培根具有极大的预见性。
我和学生常常会讨论“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的命题。我们能够非常切实地看到,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这种以物质层面的便利为全部意涵的“好”,是否经得道德层面的追问呢?答案是“未必”。以“利用”为目的认识自然,势必会使知识探求变得功利化。如此“功利”的知识探求,若随着现代商业的兴起,进一步与“利益”媾和,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吴明波老师:
《新大西岛》带给我一种比较突出的感受,就是它和我们现代的生活有种特别的亲近感。萨罗门学院的设置和很多现代学院的部门设计特别接近,岛上的宗教宽容也与现代社会对宗教的态度极为相似。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培根的这部作品与我们自己时代之间的亲缘关系。
双洪老师的讲座指引着我们从四个方面关注这部作品:
其一,这是一个以科学为内核的“拯救”故事。故事开篇便呈现了一个在《奥德赛》(Odyssey)等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场景:船员们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漂泊,而灾难在某一刻突然降临。“海难”意味着苦难与命运,就这一维度而言,新大西岛是大海中无助者的“拯救”,《新大西岛》也因而可以被理解为有关拯救的故事。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船员们最终的最终去留,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们被科学拯救,又逐渐被科学吸引。其二,作品不但与柏拉图的《克里底亚》有潜在关联,也与《理想国》(The Republic)有关,我之后会详细谈谈这一点。其三,我们也可以将之与莫尔的《乌托邦》联系起来阅读。其四,这篇故事的基督教外壳值得关注。《新大西岛》始终披着基督教的外壳,但却抽离了基督教的根基。
我还想谈一谈有关政制与知识的问题。《新大西岛》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重要的联系。《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也建立了一个言辞上的理想城邦。如果我们只读培根的《新大西岛》,或许会觉得它似乎很正常,因为文中所述与我们的生活太过相似。但是,如果我们同时阅读柏拉图《理想国》,就会发现问题。两部作品对政制,即“如何统治”问题的讨论尤为不同。《理想国》的关键点,我认为是有关最佳政制和正义城邦的讨论,而这些问题则明显在《新大西岛》中缺席,培根实际上借助“科学”,处理了这些问题。
基于这一点,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是自然差异问题。《理想国》中的理想城邦注重个体的差异,会按照个体自然性的差异分配不同的身份职责,一人一役。但在《新大西岛》中,这种差异是不存在的。人之自然差异的缺席,本质上指向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问题的缺失:什么样的人适合统治?
其次是命运问题。在《理想国》中,哲人王统治的城邦无法实现,与命运有一定的关联。只有当哲人愿意成为王,且城邦民也同意哲人成为王时,哲人的统治才能实现,但是两者很难同时达到。城邦的衰败也与命运相关。命运是城邦政治中极不稳定的因素,而新大西岛的特点即是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来源于对命运的克服。上述迥异的命运观呈现出培根与柏拉图之诉求的重大差异,也呈现出古今政治观念的显著差异。
我们回到之前对故事中宗教外壳的讨论。新大西岛中有非常明显的宗教元素,但是纵观此岛,但见基督教的发现与获得,或是岛上的神职人员,却不见基督教的核心问题——“罪与罚”,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本质上指向新大西岛中人之“善与恶”的缺失。故而,新大西岛颠覆了古典的政治观念,也颠覆了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仅保留了两者的外壳。这对我们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关注点。
上述思考其实带我们回到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政治体应当追求什么?新大西岛所追求的是身体上的舒适和幸福,而无关乎精神生活。这也表明,如果完全依靠科学,我们只能获得身体上的舒适,却无法获得精神与灵魂的充盈。将培根与柏拉图的作品互为参照,我们能够看到古今之别,从而读到更丰富的思想意涵。联系我们自己当下的生活,当我们过得特别舒适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想一想,这种“舒适”是否存在问题?
黄薇薇老师:
明波老师的评议非常精彩。谈到《新大西岛》,我最初想到的还是它与《蒂迈欧》、《克里底亚》的对堪。《蒂迈欧》与《克里底亚》两个残篇以“而且”首尾相接,一同被作为《理想国》的姊妹篇。明波老师谈到《理想国》构画了言辞中的城邦,甚至可以看成乌托邦的最早雏形。确实,在《理想国》中,格劳孔曾要求苏格拉底不要始终在言辞中建立城邦,而要说明理想城邦如何能够建立在现实之中(《理想国》471c3-474b2),而苏格拉底却转而开始讨论战争和政制的堕落。在《蒂迈欧》和《克里底亚》中,柏拉图才让苏格拉底继续讨论了《理想国》中的未竟之事,讲述现实中的理想城邦,即被洪水淹没的大西岛,以及与之相关的宇宙论。明波老师将培根与柏拉图的对堪向前推进了一步,让我们意识到新大西岛中“谁来统治”问题的缺失。我们通过新大西岛中萨罗门学院的统治,看到了培根非常坚定地展现了科学最高法权的正当性,但古典政治哲学不曾将最适合统治的人论述为最懂科学的人。
李向利老师:
双洪老师的演讲和老师们的讨论给我很大启发。我们必须承认,对民族或共同体而言,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培根对科学的讨论却并非纯粹针对科学本身,而是包含强烈的政治意图。正如双洪老师所说,培根要为政治共同体找寻平衡状态。这让我想到了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论科学和文艺》(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卢梭的这篇应征文意在回答一个问题:“复兴科学和文艺是否有助于纯化道德风尚”(Ha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ciences and arts contributed to the purification of morals?)。在解释科学文艺与道德的关系时,卢梭旁征博引,博古通今,向启蒙同道们指出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区分,并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批评科学与文艺,认为它们不利于群众德性的培养,不应该向群众普及。
双洪老师指出,培根《新大西岛》涉及“谁来统治”与“如何统治”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立足于深厚的学术背景。我们知道,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中,俄狄浦斯王智性极高,他一直在追求真相,如哲人一直在追求真理。但是,这种仅仅依靠知识来进行的统治,却有损于政治共同体的根基。柏拉图也在作品中回应了这一点,就像双洪老师提到,柏拉图《蒂迈欧》和《克里底亚》指出人是不完美的,会遭到神谴。
双洪老师提到新大西岛中依靠欲望和恐惧统治——现代哲人后来极力强调普通人的欲望和恐惧——而对人的德性避而不谈。如同马基雅维利,培根关注的是人实际什么样,而不是人应该怎么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对荷马的众神和英雄展开批评,认为荷马描写阿基琉斯的“不节制”和“恐惧”,无助于民众的德性教化。由此,我们看到,古典哲人往往都非常注重德性,而培根《新大西岛》却并不注重德性,那么生活在如此政治体中的人,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在上一场讲座中,张毅老师为我们解读了《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里面涉及到“道”与“技”的关系。庖丁精湛的“技”实际上源于他所遵循的“道”。虽然庄子之“道”并非指的是“道德”,但道与技的关系,与这里科学与德性的讨论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比如,我们现在很强调法治,这意味着把传统的较高的德性标准,降低到了“不犯法”这个较低的水准。但是,如果学者们只研究人的欲望与恐惧,如果共同体中的人都只关心科学技术与经济实力,而将德性修养置之脑后,将道德要求消极等同于“不犯法”,这势必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王双洪老师:
向利老师讲到卢梭的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卢梭确实谈到了启蒙以来学者一直要面对的问题。就政治哲学的维度而言,古典与现代非常重要的区分是:古典关注人应当是什么样的,而现代只关注人真实的样子。
法律能够规定什么事情不能做,但却不能给人以向善的指引,也不能告诉人们要如何做才算是一个好人。法律仅要求人的底线,而教育要求人“向上”。刚才我们讨论到本撒冷岛如何让群众幸福,但我认为,培根在《新大西岛》中并没有谈到幸福,而仅仅强调了秩序。这座岛上的统治,不论是借助基督教外壳,还是自然习俗中的父权,均是为了保证人们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并以此来维持民众的秩序。也就是说,新大西岛中是没有“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