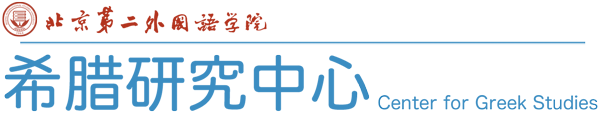摘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叙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批评,值得后世学人深思:柏拉图以诗作批评的方式维护诸神的正义,显然不同于莱布尼茨用逻各斯证明神义论的做法,理据何在?不过,后者逻各斯化神义论的做法并不成功,遭遇激烈批评。柏拉图叙述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批评,让后世读者认识到破坏神之正义的真正凶手是人们对自然的探究欲望(哲学);同时,又借助苏格拉底对几位谈话者的引导,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神义”与众人灵魂的内在关系。最终我们发现,柏拉图的“神义论”叙事(诗)——苏格拉底的荷马批评,比莱布尼茨更好地维护了诸神的正义。
关键词:柏拉图;荷马批评;莱布尼茨;神义论。
本文源起于一个质朴的问题:伟大的古希腊诗人——荷马(若真有其人的话),其作品风云诡谲、名震古今,为何却遭遇了诸多批评。其中,最有名的批评出现在哲人柏拉图的笔下,他既提到荷马是第一位悲剧诗人,同时又记叙了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批评,这似乎给人留下言辞自相矛盾的印象。苏格拉底的所有荷马批评,尤以《理想国》卷二到卷三的内容至关紧要, 它是后来讨论诗与哲学之争的基础。 国内早有学者注意到,卷二至卷三的这段荷马批评涉及教育问题,而本研究要接续这一研究方向,细致绎读该段文字,以寻找苏格拉底的荷马批评的立论依据。
一 古今神义论
苏格拉底的这段荷马批评,始终围绕着维护诸神正义一事,与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神义论》一书中从逻格斯角度证明诸神的正义殊途同归。莱布尼茨终身关注着神之正义的问题,以至于到1716年11月14日,莱布尼茨于汉诺威孤独离世之时,他所写《神义论》一书成为其生前出版过的唯一一部著作。也正是在这本书中,“神义论(theodicy)”一词才首次出现,该词由两个希腊语合成,theo出自希腊语Θεός,意指“神”;dicy即希腊语的δίκη,意指“正义、审判或辩护”。因此,“神义论”字面意指“神之正义”,或“为神辩护”等意,即面对人世间的各式罪恶,种种苦难,用各种方式证明神之正义。莱布尼茨关于神义论的想法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在1686年,四十岁的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在给恩斯特伯爵(Ernest,Landgrave of Hesse-Rheinfels)写信之时,就已经提到了“神义论”问题;他在信中介绍了自己的《论形而上学》(“Discours de metaphysique”),谈到了诸如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恶之起源、灵魂不朽等此类哲学问题,《神义论》一书的主要线索就已经出现。最初,莱布尼茨未将这些思索整理成书,直到1710年,莱布尼茨为了回应来自怀疑论者培尔(Pierre Bayle)的诘难,同时也为了纪念自己的好友夏洛特公主(Sophie Charlotte)才出版了该书。
18世纪,随着《神义论》各译本相继问世,该书为莱布尼茨赢得了巨大声名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当年,莱布尼茨与培尔的争论并没有完结。莱布尼茨以为,世上之恶并非现实的存在,而是创造物本身固有的缺失和缺陷。人本质上的有限性即属于这类缺陷,它决定了人的一切言行。人的有限性和一切创造物的不完美性成为形而上的恶,以解释苦难与罪的存在。人的罪与恶均存在于个体自由领域之内,而神的存在却高于这个领域。人世的恶无法为人的理智所解,这也恰好证实了神高于理智。不过,莱布尼茨的论述根本无法说服培尔,他早就知道这种“高于理智”与“有违理智”之间的区分。先验的(priori)区分无法回应后验的(posteriori)恶之现实,莱布尼茨这种论证,与活生生的经验难以相符,显得绵软乏力。据培尔所述,我们的理智使我们拥有次序的概念,此概念使我们认为任何自足、必然和永恒的事物都必须拥有所有可能的完美,包括至高的权能和至高的善,此即是培尔的先验理智;恶是一种现象,他被我们所经验,此即后验的理智。 莱布尼茨以为,先验理智与后验理智之间的不合是由于先验理智无法体识超越于理智之上的事物,而这需要借助于启示。但启示又无法被人的理智所获知,因此只能借助于神圣的智识。据此,莱布尼茨对理智加以区分,他所理解的理智可以产生两种真理,即“混合的真理”和“纯粹的真理”,前者的实际内容是由经验和传统所提供,其中的内在关系由理智负责处理;而后者的实际内容则是由独立于经验的理智所提供,其中一切内容均属纯粹理智。莱布尼茨认为,人的自由意志的误用应该对尘世间的恶负责,并称言启示的真理高于理智。然而,莱布尼茨的神义论在面对尘世之恶论证神之正义时,仍显得无力,其神义论仍然无法消解尘世之恶;毕竟是至高无尚的神制作出了有能力为恶的人类理智。培尔的确抓住了莱布尼茨神义论的要害。
莱布尼茨神义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神义论本身的失败。古代哲人的神义论所取得的成功为启蒙哲人的风潮所淹没,渐次为后人所遗忘。与莱布尼茨所尝试的逻各斯化的神义论做法不同,柏拉图是以叙述苏格拉底对荷马进行批评的方式来维护“神之正义”的。换言之,柏拉图是以戏剧的方式,而非以逻各斯化的方式来维护希腊诸神的正义,以实现自己的神义论关怀。不仅如此,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是以批评荷马诗作的方式来维护诸神正义。可见,古代哲人的神义论绝非一套逻各斯化的理性论述。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批评是对“诗”的改进,而柏拉图“叙述”苏格拉底的言辞,这一叙述本身同样是“诗”。古代哲人的神义论与“诗”的关系密不可分。
柏拉图叙述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批评,出现在《理想国》论述城邦卫士的教育的文段之中,显得意味深长。《理想国》记叙了苏格拉底与众人谈话的几段戏剧场景,组合而成一篇长篇对话。全书共分作十卷,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则依据其内在逻辑将其划分为序言、导论、结论和尾声四个部分:序言引出了正义问题;导论则处理了城邦的起源及制度、理念的具体化以及城邦的堕落三个问题;结论则是正义好于不义;尾声主要用灵魂不朽继续为正义张目。 全书均与城邦的政治生活相关,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它还直接与保护城邦安全的卫士教育直接相关。古代哲人维护诸神正义的语境是为城邦提供优秀的卫士。
本文所涉及的376d5-383c7属于导论部分,对话者主要谈到建立城邦的问题时提到城邦需要城邦卫士。在讨论如何教育这些卫士时,苏格拉底引导阿德曼托斯(Ademantus)展开了对荷马诗作的批评。苏格拉底的这段荷马批评可分作三个层次,第一个部分(376d5-377e5)是引入,他先谈及了真实的故事与虚假的故事之间的区分;第二个部分(377e6-378e3)主要论述了赫西俄德与荷马两位诗人笔下诸神的混乱;第三个部分(378e5-383c5)所谈的内容较多,主要是苏格拉底引导阿德曼托斯承认,应该删除诗人笔下那些与神之至善形象不相符合的内容。借由这三个部分的谈话,苏格拉底成功地超越了现世的生活,把目光投向彼岸世界。问题是苏格拉底的这一神义论方法何以奏效,而莱布尼茨的神义论逻各斯论证之途又何以遭遇困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要思考苏格拉底对荷马批评的细节及其根由;苏格拉底对荷马批评的前一段内容论述了神之正义走向式微的关键,即哲学探究所引发的诗文式微;后一段内容引导阿德曼托斯删除诗作中不符合神之正义的内容,实则隐含地指明了人对神之正义的需求,对这种需求的保护才是苏格拉底维护神之正义成功的关键。
二、隐匿的哲学
苏格拉底首先与阿德曼托斯谈及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和诸神间的不和(377e6-378a6):
“首先,”我说,“最大的、有关宇宙中最重要的事物的那个谎言,说这故事的人并没有把它编造好,声称,乌拉诺斯干出了那种事情,如赫西俄德所说,接着,克罗诺斯反过来又如何惩罚了他。克罗诺斯的行为以及他后来从儿子那里受到的遭遇,……。”
苏格拉底所提到的“事情”属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伟大家族——提坦家族的故事。此处的提坦神指大地该亚和天神乌拉诺斯的孩子,名叫克罗诺斯,而克罗诺斯又生下了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诸神。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详细记录了与提坦家族相关的神话,包括提坦的诞生(行133-138)、提坦与天神乌拉诺斯之争(行154-181)以及提坦的后代(行337-616),这些正属于赫西俄德《神谱》中的核心内容。诗人赫西俄德在古希腊不仅仅是诗人,他所讲的故事还影响着古希腊的基本宗教态度,同时还是后世研究古希腊宗教的依托。 他和荷马共同塑造着古希腊的宗教世界,但两位诗人诗作的内在品质却迥然不同。佚名作者以《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竞赛》一文记叙了二人之间的比赛。其中,赫西俄德以关注普通人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艺而获胜,荷马则因演述战争而败北。 知识和技艺服务于生活,必以对自然世界的探究为基础;赫西俄德的诗作一方面关注知识和技艺,另一方面便会系统呈现对诸神与人类宇宙存在和生成本质的研究。系统呈现万物的本质属自然学研究,成为赫西俄德诗作的宇宙视野基础。由于以自然学研究为根基,自然存在的虚空性和无目的性导致赫西俄德的宇宙学中不会包含目的论因素;所以,其故事中的诸神行为也并不指向最终之善,而是充斥着混乱。苏格拉底批评赫西俄德的故事,意在挑明这种混乱不符合城邦卫士教育的要求。自然宇宙学所发现的那个混乱的虚空与无意义,解构了荷马笔下的诸神之正义,会导致城邦卫士的教育失效。
赫西俄德诗作教育的失效如何产生?吴雅凌的研究揭示了赫西俄德笔下的英雄叙事更具人性色彩,其中普罗米修斯与厄庇米修斯的故事更是全面呈现了神人之分。 在神人未分之际,人之存在的意义由诸神提供,个人的存在问题被诸神之义所掩盖;神人分离发生之后,个人需要寻找新的存在意义。神人之分让个人的自我意识突显。赫西俄德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呈现个人自身的存在, 会对城邦卫士形成不良的影响。城邦卫士的人生意义应当由城邦赋予,他们才能献身于拱卫城邦安全的志业中。赫西俄德诗作的自然哲学品质显然与此要求不符,苏格拉底批评赫西俄德的诗作,正是要去除自然哲学对城邦卫士的影响,让他们重回城邦的存在意义之中。
在古希腊,城邦的存在意义取决于古希腊宗教。那时,不仅盛行多神崇拜,且又神人同形,形态多样。这种多样化的形态为艺术家和诗人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于是,古希腊宗教表现为从圣殿至祭仪,从祭仪到神话学的发展转变形态。 由于祭仪与城邦的关联,诗人所制作的神话故事便会影响城邦的政治生活。诗人们制作关于过去的故事并非述史,反而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要引导读者超越尘世的时间和空间,去认知不可知的美好。赫西俄德那基于自然哲学的诗作叙述,已让不可知的美好蒙上尘垢,让旧日众神的光芒不再闪耀。
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批评得到了柏拉图的理解和回应。既然关于可见宇宙的自然研究会造成个人的存在意义发生变化,所以柏拉图在叙述苏格拉底与阿德曼托斯的交谈时全然不提可见的宇宙诸神(即日月星辰之类);柏拉图显然对宇宙诸神同样具有广博的知识,他在《蒂迈欧》(Timaeus;40d3-41a5)中就同时提到了两类神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维护诸神正义的做法的理解是隐藏关于自然学的研究,突显城邦政治的内容。让自然哲学成为隐秘的学说,而让政治教育成为显白的表述。
苏格拉底的对话是柏拉图“制作”的故事,这种“制作”即是“将事迹整合到一起”(亚里士多德《诗学》1450a4-5),充分利用青年人的闲暇时光,抑制超越事物表面领会事物的强烈爱欲,然后对这样的青年人施加影响(《理想国》376d9)。在柏拉图的制作中,苏格拉底与阿德曼托斯谈论诗作,而非与格劳孔,主要在于格劳孔生性勇敢坚韧,而阿得曼托斯则生性喜好安逸快乐:
格劳孔勇敢,阿德曼托斯则节制;格劳孔转向自然,阿德曼托斯则转向意见;格劳孔注意他所看到的,阿德曼托斯则注意他所听到的。阿德曼托斯特别沉溺于诗歌。
格劳孔勇猛精进并倾向于自然的学问,可能会视诗歌中所述的故事为虚假;阿德曼托斯的性情决定他会更亲近诗作,更注重维护习传的意见,他潜意识中能把维护正义与追求智慧的爱欲相分离。尽管追求智慧的爱欲与追求奢华的爱欲品质不同,但这两种追求均属于爱欲。奢华城邦的建立是基于人对不必要之物的爱欲,即那种对身体之善毫无作用之物的爱欲,而奢华城邦的极致状态就是人能够完全释放这种爱欲。格劳孔的爱欲对于城邦的生活并不必要,反而激起了人内心的各式爱欲,引发人内心的不满与纷争,最终引发战争。由此,苏格拉底替换谈话对象,以隐藏格劳孔的爱欲,而张扬阿德曼托斯对诗的爱欲,最终格劳孔那种对自然宇宙探究的爱欲就被阿德曼托斯对美好事物(诗)的爱欲所替代了。苏格拉底对话者的转变不仅是他们从自然宇宙论到维护神之正义(即古代神义论)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谈话从追问诸神的真实到制作关于诸神的高贵谎言的转变。
从苏格拉底的做法来看,他隐藏了哲学的诉求,而推崇关于诸神的高贵谎言。柏拉图承继苏格拉底的做法,以制作戏剧对话而非哲学论述的方式书写传世之作。因此,柏拉图所制作的苏格拉底言辞首重的是文学文本独特的品格,并在这样的品格之中深藏着思想意涵。后世学人重新重视柏拉图文本的文学特征,隐藏哲学诉求,传承了苏格拉底的做法。 而若是有学者意图从文学文本之外构筑一套“学说”,将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品质逻各斯化,恰恰与苏格拉底的做法不相符。毕竟,我们可以总结说,是关于美好事物的言说,而非关于真理的论说引导着城邦卫士的灵魂献身于城邦的功业之中。
苏格拉底对赫西俄德诗作核心内容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了这类诗作对于城邦卫士的教育意义。隐藏哲学的论述是这一批评的标准所在。不过,与赫西俄德不同,荷马基于神性的诗艺超越了希腊各地方祭礼的地域性,具有泛希腊性质。这使荷马的诗作不同于其他战争传统,即荷马具有整合散乱政治生活,重塑政治共同体的整一性,这必然要求诗作的内容要具有超越尘世的宗教色彩,以认识不可知的美好。荷马将曾经散乱的传统英雄故事整合起来,并以超越尘世的诸神为根基,重塑了泛希腊地区的政治生活。 然而,荷马笔下的诸神还不够至善,苏格拉底说(378b7-378e3):
所有这一切,说什么这帮天神如何与那帮天神竞争、耍阴谋、交战——因为这些都不真实——如果我们有必要让将来这批守护城邦的卫士认为相互之间轻易结仇是最羞耻的事——远没有什么必要对他们渲染基干忒斯战争,以及天神们和英雄们对自己的亲戚和家属所抱的各种各样的仇恨——相反,……赫拉被她儿子捆住,赫菲斯托斯被他父亲抛弃,因为赫菲斯托斯想帮助挨打的母亲,以及荷马描述的天神之间的一系列斗争,这些一律都不可在城邦中流传,不管此类故事含有寓意或没有寓意。
与对赫西俄德的批评不同,苏格拉底的荷马批评并不涉及荷马作品的主干内容,即“阿喀琉斯的愤怒”与“奥德修斯的归航”。然而,荷马笔下的诸神还不够至善,显得有些混乱,而这种混乱已不同于宇宙神与城邦神的差异所造成的混乱了。苏格拉底对荷马诗作的修改,实质上是要借助荷马笔下的诸神,重新认识真正至善的诸神。他斩断了其笔下诸神混乱的本质,即诸神与尘世混乱之偶然的所有关系;若按其做法,荷马诗作中最纯粹的神性将得以保留,这也为后世发现荷马诗作之中蕴含的基督因素提供了契机。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批评显然不只是要隐藏哲学诉求,毕竟荷马诗作之中自然与哲学似乎从没有出现过,这一批评显得是要更好地维护至善诸神,以教育城邦卫士,引导他们的灵魂,献身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为何城邦卫士的灵魂需要至善的诸神?
三、灵魂诗术
苏格拉底举了两个例子(基干忒斯之间的内战以及赫拉、赫菲斯托斯与宙斯之间的战争)来说明荷马不应该叙述诸神之间的混战。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先引导阿德曼托斯得出天神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起源,然后指出应该在荷马诗作中删除荷马关于天神对人类厄运的安排(379d1-379e2),而不应该描绘神与人间纷争的关联,也不应该描绘神之间的纷争(379e2-380a1),更不该把人间的重大灾难和混乱归咎于神(380a3-4),包括“尼奥蓓的命运”、“佩洛普斯家族的命运”以及 “特洛亚的命运”。苏格拉底的批评(主要涉及荷马,部份涉及埃斯库洛斯)开启了阿德曼托斯的神义论认知,即如何认识诸神。
苏格拉底对诗人的批评,实质上构筑了神法的两项内容。第一神法的内容可总结如下:诸神作为超人类的存在,完美无缺。第二神法包含两条内容:其一,诸神不会随意改变他的样子或外形(eidos),也就是说神不会拥有多种形态,或改变样子;其二,诸神不会欺骗或撒谎。这两条神法的现场对话者是阿德曼托斯,苏格拉底一向以知人善辩著称,他并不随意与人交谈。而在此处,苏格拉底不仅与阿德曼托斯交谈,更与其共同总结了两条神法,那必定是阿德曼托斯自身的某种独特之处吸引了苏格拉底。我们借助人的言行和行动能认识一个人的性情,或称之为灵魂;我们唯有辨识出阿德曼托斯的灵魂,才能真正理解苏格拉底通过荷马批评而提出的两种神法的基本意义。然而,在《理想国》中,阿德曼托斯除了对诗极其热爱外,似乎并无太多其他明显的行动。但柏拉图为我们了解阿德曼托斯的灵魂提供了隐秘的线索。在327c1中,柏拉图安排苏格拉底叙述说:
没多久,珀勒马科斯来了,还有格劳孔的哥哥阿德曼托斯……,以及其他一些人,显然都来自游行。
在449b1-7中,苏格拉底叙述说:
珀勒马科斯——因为他坐得比阿德曼托斯稍微远一点——伸出手,抓住后者肩头上的衣服,一边把对方往后拉,一边自己凑上前去,俯身说了一阵,我们其他什么都没有听到……
阿德曼托斯总与珀勒马科斯形影不离,仿佛是柏拉图在写作中刻意安排。从全文的情节来看,苏格拉底参与此次对话显然并非完全自愿,而迫使苏格拉底参与当晚对话的正是珀勒马科斯(Polemarchus)。他名字的希腊语意思是:“军阀”、或“好战者”或“战争之主”(the War Lord)。珀勒马科斯以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强迫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留在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而苏格拉底则回应珀勒马科斯该用劝服而非强力;但苏格拉底能言善辩,珀勒马科斯无法用言辞劝苏格拉底留下,所以珀勒马科斯说若听者拒绝聆听,劝服就丝毫无法起作用。局面僵持之际,阿德曼托斯开始诉诸劝服,他告知苏格拉底这里会有敬神的火炬比赛,劝苏格拉底留下一观。尽管阿德曼托斯的关注点是新奇的火炬表演和通霄达旦的狂欢所带来的享乐生活,不过他的确起到了劝服苏格拉底留下的作用(372c-328b)。可苏格拉底并没有像阿德曼托斯说的那样,在比雷埃夫斯港走向享乐的生活,而是与众人谈论究竟何为正义。正是在他们的言谈之中,我们见到阿德曼托斯与珀勒马科斯的个性互相映衬。
首先,珀勒马科斯和阿德曼托斯都不再相信父辈们执守的对诸神的虔敬。克法洛斯(Cephalus)的正义观以全知全能的诸神为根基,而珀勒马科斯把政治生活之中的正义理解为一种技艺,以正确地扶友损敌,就如同某种战争的技艺一样(332e4-6)。政治生活中正义概念的技艺化使得操控他人、占取利益的政治阴谋成为正确的方式,珀勒马科斯比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及格劳孔更明显地预示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到来。 苏格拉底接着引导珀勒马科斯把正义问题的理解引向和平时期,正义的扶友损敌就转变成了守卫财富、预防窃贼;正义之士需要懂得偷窃之术方才能更好地保卫财富,故而正义的技艺等同于偷窃的技艺,而后者显然是不正义的(333e1-334a9)。珀勒马科斯没有预料到正义沦为技艺之后,由于技艺的非道德性,技艺同时具有的伤害(blaptein)能力会逐渐脱离道德的束缚。珀勒马科斯并不愿意追求非正义,而是意图超越道德的视域,这种超越从未发生在珀勒马科斯的父亲克法洛斯身上,因为他父亲的绝对正义是由全能的诸神所提供的。在过去,全能的诸神出现在荷马诗作之中,不过这类诗作已被视作“虚假的故事”(377d5)。荷马所撰写的诸神受到了质疑,使得诗作本身的神圣性退场,恰如克法洛斯的退场一样。所以,最终珀勒马科斯和阿德曼托斯均站到了反传统的立场之上。
其次,阿德曼托斯又不同于珀勒马科斯。珀勒马科斯拒绝劝服,显得比阿德曼托斯更有力量(327c10-12)。阿德曼托斯有对诗作的热爱,爱欲意味着某种欠缺和不完满,不完满显示的正是人生的脆弱。苏格拉底觉得知识应该为脆弱不堪的生命提供道德支撑,以托起虚弱无力的生命状态,“知识即德性”的古旧命题要战胜“知识与强力”之间的联姻。珀勒马科斯虽然强有力,但却容易陷入不道德的困境;阿德曼托斯充满爱欲,需要超越人类的诸神存在,但却也不得不面对“诸神并不真实”的挑战。苏格拉底用“知识即德性”的实践回应了珀勒马科斯和阿德曼托斯的双重困惑:苏格拉底主导着的关于正义的讨论,从下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使大家完全忘记了最开始所提到的火炬奇观,甚至对晚餐也只字未提。苏格拉底虚构的城邦建造计划掩盖了众人自然的需求——苏格拉底制作的言辞(诗)战胜了自然,赢得了人心,使得身边人忘记了放纵爱欲式的生活。从《理想国》第五卷开始,讨论进入到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在这一部分,夜幕降临,出自太阳的自然光完全消失,而他们的讨论则是完全在人为的光照之中进行。 众人的谈话需要借助人为的灯光,隐喻着人本身不能直接暴露于真实的自然之中(哲学),必须借助人的制作技艺(诗)才能更好地生活。如同苏格拉底在前文对赫西俄德的批评一样,珀勒马科斯将正义等同于技艺是基于自然学的研究,正是自然学的研究促使技艺的发展,让珀勒马科斯领略了技艺的力量,所以他希望在关于正义的命题讨论中能用“人为的”技艺替换“不真实的”传统诸神的影响力。人离不开技艺,研究自然学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技艺,但正是由于人在天性上离不开技艺,所以人不能直接接受真实的自然。诸神的传统所具有的神圣性在自然学研究者看来不过是诗人制作的产物,然而诗人的制作正是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自然学的研究虽然推动了技艺的发展,但却也破坏了诸神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恰是人类生活所无法离开的事物。
为何人离不开这种神圣性?柏拉图用忒拉绪马霍斯(Thrasymachus)的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让珀勒马科斯遭遇言辞失败,使其陷入正义即是不义的自我矛盾之中。面对言辞的困境,珀勒马科斯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引发了忒拉绪马霍斯的愤怒(336b1-6):
那位忒拉绪马霍斯,当我们还在交谈的时候,他曾多次试图插话,但随即受到坐在他身边的那几个人的阻拦,因为他们想听完我们的争论。当我们停了一下,我把话刚说完,他再也忍不住沉默,只见他紧缩一团,如同一头野兽,腾然向我们扑来,想把我们撕碎。
这让苏格拉底和珀勒马科斯均发起慌来(336b6),但苏格拉底似乎又迅速恢复了沉静,仿佛他对珀勒马科斯的行为早有预料(336d5-336e1)。接着,苏格拉底开始与这位坚持“正义即是强者的利益”的勇猛之士进行了一长段对话。珀勒马科斯没有料到他与苏格拉底的交谈会引发忒拉绪马霍斯这么大的愤怒。不过,读者却可借此知晓,苏格拉底的言辞诱发了忒拉绪马霍斯的行动。
珀勒马科斯把正义等同于人为之技艺,取消了政治生活不容质疑的神圣性。苏格拉底质疑珀勒马科斯的观念,从而引发忒拉绪马霍斯的强烈反应,这恰恰证实了证实忒拉绪马霍斯比珀勒马科斯更急迫地需要这种不容质疑的神圣性。作为父辈的克法洛斯的政治生活神圣性由诸神所提供,而自然哲学的研究让这种神圣性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珀勒马科斯推崇技艺的观念恰是自然学取代荷马诗作影响的标志,而忒拉绪马霍斯所持有的观念,即正义属强者的利益又以珀勒马科斯的观念为基础——正义意味着某种善谋的技艺(真正的强者)。
苏格拉底对珀勒马科斯的质疑太过直接,引发了忒拉绪马科斯的情绪化反应。忒拉绪马科斯无法承受言辞上的失利,否定了珀勒马科斯关于正义是一种技艺的讲法,这也会让忒拉绪马科斯关于强者利益的说法失去根基。忒拉绪马科斯的愤怒是忒拉绪马科斯、珀勒马科斯和阿德曼托斯三人共同遭遇的困境:传统诸神信念失序后的政治生存问题。传统政治生活所遭遇的挑战来自自然哲学对真理的追求,而恰恰是基于言辞的失利从而引发的愤怒证明了政治的生活而非哲学的生活才是他们的必需——追求真理之人不会在意言辞上的失利,更不会因言辞而改变自己的行动。
忒拉绪马科斯的愤怒证明,言辞无法真正解决他自身的存在问题,他需要“行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行动是动物的特有属性。人也属动物,但人的行动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具有政治属性。忒拉绪马霍斯的行动是属人的政治行动之一。人本然地就是政治的动物。然则,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本然地就是政治的动物”的论述却有诸多含混,若仅从社会交往、安全需要等现实层面来思考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则会降低该论述的形而上品质,同时也无法理解苏格拉底引导阿德曼托斯删订荷马诗作的存在本质。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存在性理解决定了他对政治的看法,人的存在并非基于肉身性的生命,而是基于某种“运动”:人的言辞和行动即是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的言行由个人灵魂中的爱欲所决定,从与苏格拉底对话者的言辞中可以清楚地见出他们对至善有不可或缺的“爱欲”,这种“爱欲”容不下质疑与否定,而恰恰是这种“爱欲”的存在证实了他们自身的欠缺,他们需要至善的诸神来弥补政治存在中的欠缺。自然哲人所追求的真实,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理解,当然他们也就无法理解政治生活对于人世的必须,会破坏掉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根基。与静观的沉思生活不同,政治生活要求人追求至善的行动,而言辞则是对这一追求的维护——苏格拉底之荷马批评的神学意蕴即在于此。苏格拉底要求删除荷马关于诸神的所有不恰当论述,而仅保留诸神的至善品质,这是对政治生活的维护。人离不开政治生活,城邦卫士需要捍卫这样的生活,他们不应该接受自然哲学对存在意义的腐蚀,而应在“诗”的呵护之下更好地献身于城邦。
结 语
据此,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在《理想国》(376d5-398b8)中,苏格拉底坚持对诗人的诗作,尤其是荷马的诗作进行修改,并非出于诗艺的考虑,也非哲学需要,而是为了维护众人共同需要的政治生活的神圣性,更是为了引导城邦卫士的灵魂不受自然哲学破坏。苏格拉底没有像后世的哲人,如莱布尼茨一样,将“神义”逻各斯化,以转化为论述,而是采用“与人交谈”这种具有政治实践特色的做法维护神的正义。柏拉图制作关于“苏格拉底言行”的戏剧,而非以论述的方式直陈哲学观念,目的同样是隐藏“求真”爱欲对政治生活的破坏,从而更好地引导后世的城邦卫士献身于共同体的政治生活。柏拉图的神义论是对苏格拉底言行的制作,是一种“诗”,这是柏拉图不同于莱布尼茨的地方,也是古代神义论的真正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联合培养博士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希腊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The Theodicy of Plato
—Analysis on the Critics of Socrates towards Homer in Republic (376d5- 383c7)
By Cui Wei
Abstract: Plato narrates Socrates’ critics on Homer in his Republic and it is worthy to consider the reasons why Plato’s poetic way of defending the justice of god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way of Leibniz who attempt to prove theodicy through Logos; however, the failure of Leibniz is obvious and it also suffers a lot of critics. The narration of Socrates’ critics on Homer in Plato’s writing make the audiences realize that the true assailant of theodicy is the desire of inquiring nature (philosophy); meanwhile, the guidance of Socrates among interlocutors lead the readers step deeply into the recogniti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just of gods and the soul of human beings. Finally, we realize that the narrative poem--the critics of Socrates on Homer--towards the justice of gods is better for defending the justice of gods than Leibniz’s way.
Key words: Plato; Critics on Homer; Leibniz; theodicy